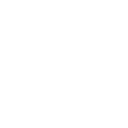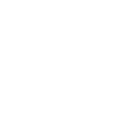“念完诗,课就散,顾城准备撤,谢烨自然上前呵护,温情地将一条长围脖为她的男人围好,仿佛围住了顾城的一生。”
对顾城怎样评价怎样缅怀,是一件让整个中国文坛尴尬的事情。他的诔文到底该以罪行开头还是以艺术开头呢?艺术至上显得不近人情,伦理之上又显得保守,北岛新出的顾城回忆录里的每一个执笔的作家无一不是欲说还休,努力躲避着这个悲剧的伦理核心。
阳光的阴影一样存在于人性中的恶是那样常见,每个人鲜活的肉体中都不停地进行着死,健康的细胞与坏掉的细胞时时刻刻保持同在,又保持斗争。顾城原本可以与他身体里恶的一面稳定地活下去,甚至与他握手言和,只是谢烨在一开始放纵了他的恶,却在最后给予了他的恶最致命的挑衅。谢烨已然仁至义尽,但不得不说她不明白怎样对顾城是最好,顾城童真,于是谢烨便放纵他的任性;顾城才华横溢,谢烨便任由顾城在这份感情中的一味索取。一切的一切都是错位的,谢烨只是在盲目崇拜顾城的才华,把顾城所有怪异的不合时宜的行为作为才华的附属物统统接受。谢烨包容,可惜也只有包容。看过顾城访谈的人应该都知道顾城是很有理性,具有洞见,完全不幼稚的人,可是谢烨却放弃了把顾城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选择,只把他当成一个物来供养着。
有的人的确需要引导,需要扎实的教训,这不会对才华有任何损失,因为我们的确发现,顾城的新西兰时期的诗歌水平大不如北京时期,因为那时他的心理已经蛋的生活压迫到了极点。他的才华已经偏居一隅,占领他的只剩一些神经质的呓语(见《滴滴里滴》)。顾城是被惯坏的,被妈妈惯之后被爱人惯,在这种宠溺接力中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,找到的只有迷途的悲哀。
这种悲哀本身可以避免,因为顾城的死与海子的死在性质上太不一样了,海子找到了自己,他死得其所,他死得让人舒心。而顾城呢?他是不小心坠落的,现实之箭射中了他永远不想弯下的膝盖,他姿势难堪地掉下了悬崖,是最不优雅最low的死法。九三年十月八号,他砍死谢烨上吊自杀,但是从书信中看,直到九月二十六号,他都是满怀信心想要回国好好活下去,甚至计划着为朋友的杂志写专栏,他还说以后想在小说方面有所发展!结果事情的结局蓦然变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。因为他后来知道了谢烨想推开他,谢烨受够了他,谢烨甚至让英儿与他们同住就是为了完成对顾城的转交仪式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谢烨能够忍受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的生活,因为她已经没有了对顾城的任何留恋。顾城的恶就这样被挑衅了,他受到了作为人的侮辱,他第一次知道在爱情中他被当成了物,他不假思索,他忘记一切,他失控了。而他最后的失控却仅仅是这个错位的爱情最初埋下的结局,水到渠成。顾城虽然痴迷自然和纯真天性,却没有长出自己的保护壳,在谢烨无微不至的保护下,他的皮肤是那样弱不禁风,吹弹可破。
顾城浪费了一身的才华,我曾经从他的散文出发,想象着他那静谧、跃动、通灵的语言最终成长为大河——小说的艺术,却也只能想象了。男儿身绊咏絮才,又偏偏遇上一味纵容无法自拔的爱情。尽管这是一个诗人的故事,无疑也指向了所有恋爱中的男女,这样看来,顾城悲剧中的善恶之辩并没有那么重要,历史自然会摆正善恶的天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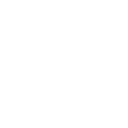

@BETHASH6